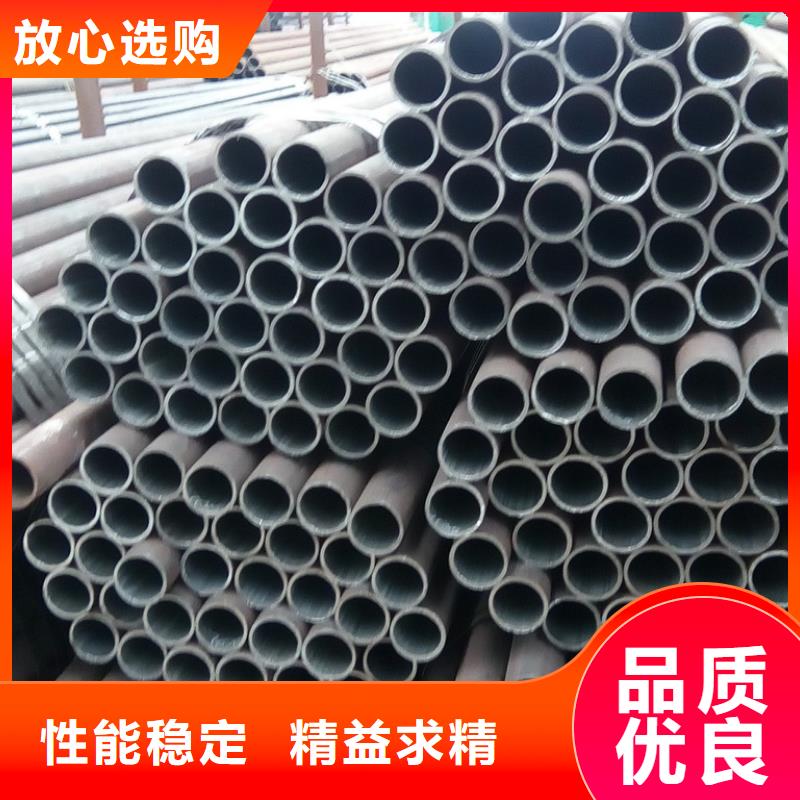
2024 年的帷幕已经落下。回首这一年,世界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曾几何时,我们以为二战后的和平与繁荣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,但是历史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,每一段稳定的背后,都暗藏着新一轮的挑战。
在这个全球格局日渐分化的时代,我们曾经熟悉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那些曾经构建起二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—— 稳定的供应链、可控的能源市场、以及国际协作精神,如今却变得支离破碎,甚至在逐渐解体。
2024 年,是全球秩序加速重构的一年。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更进一步,美元的霸权地位似乎隐隐受挫;六代机的横空出世,让军事科技的差距愈发清晰;特朗普的再度回归,为全球政坛的两极化又添了一笔浓墨重彩。
或许,100 年前的全球化承载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,而 2024 年的全球化却好似一张被撕裂的地图,分割为无数孤立的利益岛屿。
与此同时,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。从新能源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,到半导体与芯片产业的拉锯战,这一年,世界格局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:这是一个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的时代。
很多年后,当我们回望 2024,或许会发现,这一年里隐藏着重塑未来格局的无数伏笔,就像 “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” 的暗涌。
如果要用 3 个关键词代表 2024 年,那么,你最先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?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地缘经济。
这一年,地缘经济的浪潮涌动不息,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无疑是日本和德国。这两个曾经以制造业标杆自居的国家,过去几十年通过技术创新和精密的产业布局,牢牢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高价值环节。
然而,随着全球化浪潮逐渐退却,供应链呈现出加速区域化的趋势,日本与德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:一方面是内部产业升级与能源转型的巨大压力,另一方面是它们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角色愈发重要。
从德国加速布局新能源车电池技术,到日本竭力突围半导体领域,这些决策不只是为了保持各自在新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,更深刻地塑造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进程。
地缘经济的博弈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,而 2024 年的主旋律便是制造业投资的激增。这一趋势并非市场自发的选择,而是各国在战略安全、技术主导权和全球竞争三重驱动下的主动布局。
历史早已证明,制造业强国从未停止在全球经济中追逐线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,到 20 世纪美国主导的全球工业浪潮,制造业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家竞争力的象征。
二战结束时,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的 52%,这背后是其对技术、资源和产业链的全面掌控。而今天,虽然德国和日本依旧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核心地位,但在供应链区域化、新技术革命和地缘政治多重压力的叠加之下,它们所面对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。
德国,曾被誉为欧洲制造业的 “定海神针”,这一形象曾经是信心的象征,但 2024 年的德国,迎面撞上了几股力量的夹击,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。
新能源革命的浪潮、能源危机的后遗症,以及东欧制造业的快速崛起,几股力量叠加,迫使德国制造站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。曾经 “意气风发” 的德国制造业,如今似乎陷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。
尤其是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核心产业,在新能源车的浪潮中,光环正在逐步褪去。2024 年,德国汽车总产量如果保持趋势,应该是差不多 400 万辆出头,相较 2023 年的 348 万辆有所回升,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功不可没。然而,这样的增长远不足以弥补传统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带来的冲击。
与此同时,2024 年 1 - 11 月,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维持在 69.6%,其中 10 - 11 月更是达到 76%,德国的市场占比正在被一步步蚕食。
如果说新能源车的挑战是 “外患”,那么能源问题就是德国的 “内忧”。2024 年 12 月,HCOB 德国制造业 PMI 确认为 42.5,低于 10 月和 11 月的 43,制造业活动进一步收缩。
自 2024 年初以来,德国电力价格上涨了 104.12 欧元 / 兆瓦时,相当于增长了 643.51%。用电成本的高企,不仅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,还直接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。
更让人揪心的是,德国制造业的高投入并没有转化为国内消费的热情,德国国内消费的疲软更是雪上加霜。2024 年 10 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1.5%,远低于预期的 0.3% 降幅。
根据最新数据显示,2024 年第四季度,德国经济增长数据仍不乐观,预计全年 GDP 将收缩 0.2%,成为欧盟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。
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,内需疲软让整个经济失去了 “软着陆” 的缓冲力。收入高的人把钱攒起来不花,储蓄率渐渐高企;中低收入家庭则捂紧钱包,消费意愿直线下降。制造业转型带来的 “阵痛”,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德国普通人身上。
除此之外,德国还有另一块心病 —— 东欧邻居的崛起。2024 年,波兰吸引了超过 30 亿欧元的新能源汽车相关投资,同比增长 20%;而德国同期增长仅为 5%。
匈牙利的制造业工资仅为德国的 1/3,吸引了宁德时代、三星等大型投资项目,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欧洲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的地位。
资本的流向,冷冰冰地讲述着一个事实:欧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,德国已经无法独占。
然而,德国制造业的问题,看似是新能源车、能源危机、东欧竞争这些 “变量” 叠加,但深层次的原因,还是一个 “钢印” 问题。几十年技术积累带来的路径依赖,是德国制造的光环,它的背后,是一套复杂但僵化的经济模式。这套模式曾是德国崛起的基石,而如今,却也成为了阻碍其转型的枷锁。
关于日本,我们都知道,精密的机械仪器、灵巧的工业机器人,还有驰名世界的汽车品牌,这些,都曾是日本制造业引以为傲的光环,也是现今政府努力想要重现的辉煌。
而在这种荣耀之下,却隐藏着孤独。这种孤独,不仅来自于日本在高端制造领域的艰难突围,也来自于其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。
日本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,依旧体现在半导体制造设备、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附加值领域,在全球市场上,日本的精密制造设备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预估,2024 年度,日本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将首度突破 4 万亿日元,同比增长 15.0%,达到 42522 亿日元,约合人民币 1920 亿元。
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(IFR)发布的《2023 世界机器人报告》显示,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国,占全球机器人产量的 46%,领跑全球。
然而,这些数字背后的现实并不轻松。索尼集团和三菱电机等日本企业,将在 2029 年之前,展开 5 万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 2259 亿元)规模的半导体投资。日本财务省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显示,制造半导体等的信息通信机械的设备投资,2022 年度达到 2.1 万亿日元,5 年里增加了 30%。
这些投资承载着日本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,但问题在于,这些领域的特点是投资周期长、技术门槛高,其成果很难迅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。
同时,2024 年日本制造业整体表现依旧疲软。技术的孤独,背后是内需的沉寂。
2024 年,日本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29.3%,创历史新高,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老龄化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,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的消费增长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这是 1995 年到 2024 年第二季度的日本家庭储蓄率,可以看到最近几个季度,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处于低位,甚至有落入负数区间。这背后的原因,不仅仅是因为家庭支出的增加,还有收入增长停滞,以及消费者信心仍然不足。
储蓄率问题和人口老龄化,形成了内需发展的双重掣肘,即便制造业在出口市场上拼杀得风生水起,却难以改变国内经济活力不足的现状。
内需的疲软,使得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出口。数据显示,2024 年 10 月,日本的出口额为 9426.66 亿日元(约合 63.5 亿美元),而 11 月出口同比增长 3.8%,达到 9,152.38 亿日元。
这种高度外向型的经济结构看似稳定,实则脆弱。过度依赖出口市场的模式,正让日本经济处于一种微妙的脆弱平衡中。全球市场需求的波动,尤其是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压力,让日本的出口主导型经济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。
以汽车行业为例,丰田汽车在 2024 年 9 月的全球产量连续第八个月下降,同比减少 8%,至 826,556 辆。数据显示,2024 年 1 - 10 月,中国新能源车出口量达到了 172 万辆。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,日本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渐被侵蚀。
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,可以去翻看一下其他关于日本的文章,内容涵盖人口、产业、经济、日元。
地缘经济的转型,不仅仅是国家间权力博弈的战场,更是全球经济稳定的根基。在供应链被重塑的同时,价格波动成了无法忽视的副产品,从能源到粮食,再到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上升,全球化的退潮正在为通胀埋下深刻伏笔。这种压力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,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。
一代人的成功经历,最终都会成为下一代人需要挣脱的枷锁。2024 年的德国和日本,就像是在一条越来越窄的路上狂奔,几十年的辉煌为它们赢得了世界级的地位,但这些辉煌,也像一道厚重的钢印,牢牢把它们的思路钉在了原地。
通胀,是经济学里绕不开的 “永恒线 年的通胀,却有点不一样。这一年,我们见证了高通胀向低通胀的过渡,虽然全球物价正在缓步回落,但高通胀带来的冲击,远还没有结束。
各国央行的利率政策,像个紧绷的弹簧,一头连接着抑制通胀的执念,另一头却被脆弱的经济增长拉得摇摇欲坠。
1923 年,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・基钦提出过一个概念 ——基钦周期,又叫库存周期。一个典型的基钦周期以库存为标志,分为四个阶段:被动去库存、主动补库存、被动补库存、主动去库存。
回顾 2021 到 2022 年,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,被压抑的需求爆发叠加供应链瓶颈,推动全球物价飙升。
比如,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升至每桶 139.13 美元,天然气价格飙升至历史高位。
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 14% 以上,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(GSCPI)在 2022 年达到峰值。各国央行此时显得 “后知后觉”,对通胀的反应滞后。
从 2023 年开始,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进入了强力加息周期,这是通胀周期的第二阶段,政策的目标很明确 —— 抑制需求。
虽然通胀率开始下降,但高利率让消费和投资意愿双双受挫,经济增长被显著拖累。例如,尽管美联储使出浑身解数,但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起起伏伏,却始终见不到明显的起色。
与此同时,尽管通胀率下降,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 3.2%(IMF 数据),依旧低于历史平均年度增速。
进入 2024 年,通胀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,价格压力开始缓解,全球供应链逐渐修复,能源价格从高点回落。
以欧洲为例,天然气价格从 2022 年的高峰下降了 40%,全球粮食价格也下滑了约 10%。
但这种回落并非是全面的,不少服务业价格,尤其是住房、医疗和餐饮,仍保持高位,核心通胀难以彻底压低。
通胀回落后,经济的滞涨风险开始显现,这是通胀周期的最后阶段。根据联合国的报告,20224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放缓至 2.4%,低于疫情前 3% 的增长率。
欧洲的滞涨问题尤为明显,预计 2024 年欧元区增长率仅为 0.8%。其中德国和意大利,更是陷入技术性衰退,高通胀叠加低增长,成为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。美国则在高利率的长期影响下,房地产市场和耐用消费品行业深受打击。
通胀的起伏,就像是一场全球经济的测试,测的是各国如何在复杂变量中找到平衡点。从 2021 年的需求爆发,到 2024 年的价格回落,每一步都深刻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的选择。
正如基钦周期中的每个阶段都环环相扣,全球经济中的通胀治理,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:从需求过剩到供给恢复,从加息遏制到经济增速放缓。
如今,全球正处于通胀治理的关键节点,高昂的能源成本、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,以及利率政策的长期效应,都让这一局面充满了不确定性。美国和欧洲的案例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性,虽然通胀指标在逐步下降,但背后的成本正在显现:经济增长受阻、债务压力增加、社会消费疲软。
可以说,2024 年的通胀治理,既是经济的 “降温” 操作,也是一场在滞胀边缘的风险博弈。
美国,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,在 2024 年的通胀治理上,依然走得战战兢兢。
高利率像一张拉得太紧的弓,箭还没射出去,弓弦却已经快断了。美联储在全年维持了 5% 以上的高利率水平,这是自 2007 年以来最长的一次高利率周期。
但如果仔细了看,这种下降背后的代价实在让人挠头。比如经济增长,虽然 2024 年的增长率略微回升至 2.7%,比 2023 年好看了一些,但与疫情前 3% 以上的长期平均水平相比,还是差点意思。
消费者支出尤其疲软,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领域的销量,依然低迷,就算房地产市场稍微回暖,也只是 “回血未满”,距离疫情前的巅峰还差得远。
最让人揪心的,是高利率对债务市场的挤压。2024 财年,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达到了 1.1 万亿美元,比上一年增长了整整 29%。这是什么概念?这笔钱占到 GDP 的 3.93%,是 1998 年以来的最高点,几乎吃掉了联邦预算的 10%。
用个不恰当的比喻,这就好像是一位跑步的选手,膝盖还没好利索,就又背上了一袋沙子。更糟糕的是,美国的通胀还藏着 “死角”。住房租金、医疗费用和服务业价格依然 “高烧不退”。
2024 年 11 月的数据显示,住房成本环比上涨 0.3%,单这一项就贡献了当月通胀增幅的 40%,服务业价格则像一块黏在鞋底的口香糖,拉也拉不下来。
高利率虽然看起来压住了通胀,但同时也让增长的活力被锁在了冰箱里。美国在通胀治理和经济复苏之间,像是在一块湿滑的独木桥上行走,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不稳当。
欧洲央行全年维持紧缩政策,利率在 2024 年第三季度,一度达到 4% 的高位,随后逐步下调至年底的 3.15%。
尽管如此,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已经放缓至目标水平以下,9 月同比降至 1.7%,但此前长期高企的通胀压力,仍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显著影响。
数据显示,欧盟 2024 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0.7%,创近十年的最低点。其中,德国经济预计萎缩 0.2%,意大利增长乏力。作为欧洲经济的 “火车头”,德国和意大利的表现,进一步拖累了整体复苏。制造业订单和消费指数在这两个国家持续下滑,显示出经济需求端的疲软。
能源成本问题,依然是欧洲经济复苏的主要阻力。尽管天然气价格较 2022 年的历史高位有所回落,但波动性仍然较大。2024 年冬季,天然气价格出现反弹,再次对欧洲的能源依赖性提出挑战。
与此同时,欧洲的绿色转型政策,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,但在短期内,尚未完全缓解能源供需矛盾。
可以说,欧洲在通胀治理的战场上取得了一定成绩,但滞胀风险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。
印度,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,截至 11 月,年度通胀率从 10 月的 6.21% 降至 5.48%,回到印度央行设定的 4%±2% 的目标范围内。
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,然而,食品价格仍然高企,11 月的食品通胀率为 9.04%,对整体通胀形成了持续压力。
不过,挺神奇的是,这样的压力并没有完全压垮印度的消费热情。例如,2024 年第三季度,印度个人电脑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 12%,达到 630 万台,其中平板电脑出货量增长了 49%,消费者需求活跃。
政府也在努力 “帮一把”,补贴政策、税收减免,甚至对一些关键商品进行价格管控,但效果只能算是 “略见成效”。毕竟,食品通胀是个难啃的硬骨头,这背后牵动的是全球粮食市场、气候变化和印度国内供需失衡的多重矛盾。
拉美国家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。在过去的 2024 年,拉美国家继续与高通胀在作斗争,但不同国家的表现,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
阿根廷,作为拉美地区通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,它的年通胀率在 2024 年突破了 292.2%,创下历史新高。
生活必需品价格几乎失控,居民们的购买力被通胀啃得所剩无几,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一天一个样。
政府尝试过汇率控制和价格管制,但这些手段就像是在洪水中堵住一个漏洞,其他地方的水还是汹涌而至。结果呢?GDP 全年预计萎缩 3.5%,经济在衰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。
2024 年,巴西的通胀率预计为 4.1%,接近政府目标区间。巴西央行通过积极的紧缩政策和货币调控,成功将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。
然而,这种稳健的通胀治理也付出了代价。经济增长虽未陷入停滞,但扩张速度有限,预计全年 GDP 增速为 2.55%。尽管如此,巴西的表现仍显得相对稳定。
在 2024 年,阿根廷和巴西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通胀治理路径,阿根廷以极高的通胀率和经济衰退为代价,艰难维持基本市场运转;而巴西则通过严格的政策调控,压低了通胀,但经济增长也受到了限制。
2024 年的非洲经济,就像一场旱季里的长跑,粮食通胀成了背后的烈日,炙烤着民众的生活。
根据最新数据,尼日利亚,这个非洲最大的经济体,11 月的数据显示,食品通胀率飙升至 39.93%,比 10 月的 39.16% 更上一层楼。
价格上涨的主角,是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主食:大米、玉米、面包、土豆和食用油。对于一个以食品支出占家庭预算大头的国家来说,这无异于在民众的生活压力上,又加了一把重重的砝码。
尼日利亚的故事,其实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缩影。数据显示,非洲的平均通胀率预计将从 2023 年的 17% 升至 2024 年的 17.8%。推手无外乎:粮食价格居高不下,全球粮食市场供需失衡,能源价格持续波动。
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,更是一场民生危机。对于尼日利亚和许多依赖进口粮食的非洲国家来说,高昂的粮食价格,直接侵蚀了居民的消费能力,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,更加难以为继。
2024 年的通胀,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,而是一场全球经济规则的再调整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,每一次成本上涨、供应链断裂,都会带来对政策选择的更大压力。
而当这种压力,交织在地缘经济和通胀治理之中,“变量”的出现,将成为影响局势的关键。这个变量,就是特朗普。
除了地缘经济和通货膨胀之外,我想到的第三个词,是一个人名,对,就是特朗普。
特朗普的回归,就像是投入湖心的有一块巨石,激起的不是涟漪,而是滔天巨浪。
特朗普是什么?有人说他是一个谜,有人说他是变数,但在我看来,他是定数中的最大变量,Unpredictable。
他的存在,不只是一个政治现象,更像是一场无法规避的赌局。他的一举一动,可以带来新的焦虑,也可以带来新的希望。
特朗普的上台,是一场高调的逆袭,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再次抬头,也宣告外交政策从全球干涉转向战略收缩。
从贸易战到撤出国际协议,他挥舞着 “美国优先” 的旗帜,让全球化的齿轮嘎然而止,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全球角色。
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,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面貌,也让全球供应链加速分裂。“美国优先”的政策,加剧了供应链从中国等新兴市场向政治盟友转移的趋势,而这种变化,反过来强化了地缘经济的区域化特征。
回顾他的第一个任期,2018 年,他对输美商品加征关税,涵盖了 3700 亿美元的商品,这不仅在短期内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部分回流,还将全球供应链打得支离破碎。
一些人欢呼,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2018 年的约 1659.3 万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1678.4 万人,制造业产值也略有上升。
而如果说特朗普的 “孤立主义” 政策,是为了重新定义美国的全球角色,那么 MAGA 运动,则是他在国内的最大资本。
从 “草根政治” 到吸引精英,他让 MAGA 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政治的主流力量。
2024 年,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,这些曾经的蓝色票仓,因对全球化政策的不满而转为红色。这种转变,不仅表现在选票上,更体现在选民心理深处,他们对全球化的失望、对经济安全的渴望,让特朗普成为了 “最后的希望”。
他们不需要复杂的经济学模型,只要听到 “制造业回流”“关税保护”,他们的选票就会流向特朗普。
数据显示,2009 年密歇根州的失业率一度高达 14.6%,而 2024 年,这些制造业重镇的选民仍然将就业和经济复苏视为投票的核心诉求。特朗普正是抓住了这一点,通过强调 “美国优先”,成功凝聚了蓝领社区对 MAGA 的支持。
如果说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政策方向,MAGA 是政治资本,那么他的战略模糊性,则是他最大的武器。
他的一些言行,看似荒诞不经,却往往藏着更深远的意图。就像他第一任期时对内阁的大换血,推翻建制派,将忠于 “特朗普主义” 的人物扶上台,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力量。
这种 “战略模糊” 让他的对手难以捉摸,也让他的支持者相信,他是那个能够带领美国走出泥潭的人。
特朗普的重返白宫,可能会加剧这种 “模糊性”,他的政策可能更加极端,更具冲击力,也可能让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不确定阶段。
特朗普的政策就像一枚催化剂,加剧了大国之间的产业竞争。从德国的新能源车电池布局,到日本的半导体技术突围,这些国家的产业战略,在一定程度上,是对特朗普时期政策的回应。这种“应激反应”,推动了地缘经济在 2024 年的进一步加速分化。
特朗普的存在,从来不只是美国的问题,欧洲、中东、东亚,每一个地区都因为他的决策,而变得更加复杂。
对欧洲:美国减少对北约的支持,让欧洲不得不独自面对安全挑战,可内部的能源危机和财政困境,让欧洲在整合防御能力时步履维艰。
对中东:美国的战略收缩,让中东局势更加扑朔迷离,真空地带的形成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,而特朗普的 “交易外交” 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。
对东亚:特朗普的回归可能进一步激化竞争,尤其是在技术和贸易领域,而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,也会因为美国的不确定性而持续升温。
特朗普的回归,就像一场无法回避的赌局,他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孤立主义,把 MAGA 变成了政治核心力量,用战略模糊性挑战着现有的国际秩序。他让 “美国优先” 成为选民的信仰,也让全球化的齿轮嘎然而止。
如果说 2024 年是一个时代的节点,那么特朗普,就是这个节点上最大的赌局。
最近几年,“美国制造业回流”,总是被很多人挂在嘴边,很多外媒也大肆宣传,它是美国经济复兴的希望。
当时,特朗普提出 “让制造业回归美国”,并承诺通过税改和加税政策,让美国的制造业重新崛起。
然而,最终的结果大家心里都有数,很多看似光鲜的承诺,最后变成了空头支票。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计划。富士康最初承诺投资 100 亿美元,创造 13000 个工作岗位,但到了 2020 年,投资额直接缩水了 70%,工作岗位也远低于预期,最初打算建设的液晶显示屏工厂,最终也没能建成。
美国制造业的最大竞争力问题,就是劳动力成本。富士康在美国的时薪是 12 美元,在印度的时薪是 1.5 美元,8 倍的差距,要怎么竞争?
当然,这个时薪是可以通过加班提高的,比如,你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,每周休息一天,不论节假日,那么你将获得的是,最高 4 美元的时薪。
你觉得铁锈带的人听了后,他们会进厂子里工作吗?包不会的。这必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制造业回流。而且,就算他们去了,美国有劳动法,有福利要求,那你考虑过富士康的感受吗?
所以,即使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,想要制造业回流,但问题是,这不是政策就能改变的,这是全球竞争力变化的结果。
不过,制造业这个问题,也不仅仅是美国人面临的尴尬,全世界范围内,但凡是稍微有那么点钱的,人口又多的国家,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。
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,特朗普能不明白吗?或者说特朗普的团队里,没人明白吗?我相信肯定是有人明白的。
我觉得,美国真正的目的是,是不希望有国家通过工业化,继续挑战自己的全球霸权。
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制造业,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,尤其是这个国家有足够多的人,有足够强大的领导力。对于美国来说,他就会感觉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。
美国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,就已经在制造业被打的不成样子了,但打败美国的是日本吗?当然不是,那是中国吗?当然也不是。
是哈耶克的那双无形的大手,美国的强盛是因为这只手,美国的制造业衰败也是因为这只手。
时至今日,照猫画虎肯定是不行了的,直接让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停滞,或者直接封锁住,显然也是不可能的。
刚刚说了,美国碰到的劳动力成本问题,其实不是只有美国碰到的,美国其实很清楚,全球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格局,正在发生变化。
所以,美国的做法是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,削弱单一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,然后通过区域性战略,将关键制造产业链分散到新兴国家和市场。
这样不仅能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,还能确保全球制造体系中的供应链,在多国之间平衡,降低风险,保证自己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。
就比如,现在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,把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转移到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等国家了吗?
还有些措施这里就不细说了,大家懂得都懂,那些措施表面上是限制,但实际上玩的是分割。
根本原因很简单,老太太吃柿子,得挑软的捏。毕竟,相对来说,东南亚,南亚,还有拉美地区的国家,那就是软柿子了,对于美国来说,那是可以随便收割的,只要你到了那儿,那就有的是办法。
所以,美国要的是重建吗?是回流吗?不是,重建、回流,那是制造业那摊子事儿,又累又苦。
有句话叫什么来着,找问题的时候,不要只找自己有没有问题,要看能不能解决创造问题的人。
正所谓破坏要比重建容易一万倍。但是,美国似乎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情况。攘外必先安内。
现在的美国,预算赤字占 GDP 的 6%,国家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%,而且还在持续增加。
与此同时,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,一部分高学历、高技能的人群,收入可观、生活优渥;而另一部分工人阶层却在为生计而挣扎。
这部分工人阶层曾是特朗普的选民基础,但问题在于: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,其实是没办法帮他们找回工作的。
那么,在技术进步的同时,许多工作已经被机器人取代,人工智能效率更高,成本更低,带给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工人阶层来说,机器人和 AI 将取代他们的工作,带来的只是失业和收入下降。
而与此同时,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在美国,前 10 大富豪的资产已经合计达到了 1.7 万亿美元,但 30 年前,可不是这样的。
机器人和 AI 是什么产业?是需要巨量投资,是需要人才,天才,唯独不需要太多普通人的产业。
美国现在有 180 万卡车司机,这个工作的整体收入呢,都是相对不错的,网上也有一些频道有拍 vlog,有兴趣的可以去搜搜看看。但是他们知道马斯克要对他们下手了吗?如果失业了,要怎么平衡呢?那明摆着的就只能是要找富人们去征税了,毕竟富人们在整个过程中赚到了钱,那总得承担一下社会责任吧?
但是吧,特朗普是反对再分配的,对于再分配的回答就是保护主义。分配?是不可能分配的。因此,他的选择,只能是征税,向国外征税。那就又会让工人阶层的选民们,为购买日用品,支付更多的钱。你看,死循环了不是?
所以,从根本上,特朗普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制造业和工人阶层面临的困境的。
你还记得前阵子特朗普说,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吗?两个大国面对威胁时必然会发生冲突,因为要争夺全球领导权;但是,世界不是一场零和游戏,问题并非谁是第一,而是我们如何和平共处、分享繁荣。我们需要和平的时代,只不过,美国人的心态,这会儿是有问题的。Betway-官网平台Betway-官网平台

